
圖:《老照片背后的清華故事》�����,金富軍著,清華大學(xué)出版社�。
近日,香港特區(qū)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(wù)署(康文署)與清華大學(xué)校史館合作����,在香港孫中山紀(jì)念館舉行“自強(qiáng)不息 厚德載物─清華大學(xué)的人和事”專題展覽,共展出60余組/件清華校史的珍貴資料�����。對(duì)于希望進(jìn)一步了解清華的朋友來說�,閱讀校史圖書是最方便有效的方法。事實(shí)上����,清華校史如今已成專門研究領(lǐng)域,成果豐碩����。對(duì)于大眾閱讀而言��,史料扎實(shí)��、行文流暢��、圖文并茂的書籍無疑是上上之選���。在這方面,我以為�����,近年來的新作首推《老照片背后的清華故事》(金富軍著���,清華大學(xué)出版社���,2020年;以下簡稱《老照片》)�。本書融清華精神和清華歷史于一爐,以圖說史���,娓娓道來��,讀來大有收獲��。\谷中風(fēng)
本書分為“學(xué)校發(fā)展”“人才培養(yǎng)”“科研與服務(wù)”“校園文化”和“人物”等幾個(gè)板塊�。全書從小處著眼,以一張張歷史圖片引出一個(gè)個(gè)故事�,但作者心中存有清華發(fā)展大脈絡(luò),故選題取材均扣在校史的關(guān)節(jié)點(diǎn)上����。
刻畫清華精神的圖譜
開篇之作《篳路藍(lán)縷創(chuàng)校元?jiǎng)臁芬昧恕?909年第一批直接留美生合影”�����,前排居中坐著的周自齊���、范源濂和唐國安����,便是創(chuàng)校的三位領(lǐng)導(dǎo)����。《曹云祥校長奠定民主管理基礎(chǔ)》一文���,介紹了曹校長推動(dòng)教授治校在清華確立的過程��。1928年出任校長的羅家倫���,則提出“羅致良好教師�����,是大學(xué)校長第一個(gè)責(zé)任”����。正是這樣的辦學(xué)體制和人才力量����,為清華快速發(fā)展奠定了基礎(chǔ)。在清華的“校長譜”上���,梅貽琦無疑是最閃耀的一顆星�����。關(guān)于梅校長可說的實(shí)在太多了��,本書中的《大師與大樓》一篇聚焦梅貽琦“所謂大學(xué)者���,非謂有大樓之謂也���,有大師之謂也”這句名言,結(jié)合語境��,深思細(xì)研�,作出了周密而有新穎的解讀。書中指出�����,在梅貽琦看來����,設(shè)備和教授是進(jìn)行高深研究必備的兩個(gè)條件�����。但是���,他在高看“大師”的同時(shí)�����,并沒有否定“大樓”的價(jià)值�。而他所謂的“大樓”也只是形象的說法,其內(nèi)涵包括“建筑及設(shè)備方面”���。在此基礎(chǔ)上�,作者進(jìn)而指出�����,羅家倫���、竺可楨等著名的大學(xué)校長其實(shí)都有類似的思想和言論���,梅貽琦只是說出了卓越教育家群體的共識(shí)。當(dāng)代中國正走在民族復(fù)興的新征程上�����,亟需科教興國戰(zhàn)略的支撐���。在此背景下�����,閱讀書中篇什���,更覺其強(qiáng)烈的現(xiàn)實(shí)意義���。
通讀《老照片》的讀者,定會(huì)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寓清華校史于中華民族復(fù)興史的學(xué)術(shù)襟懷�����。作為在清華求學(xué)治學(xué)二十馀載又以清華校史研究為專業(yè)的學(xué)者�����,本書作者深刻洞悉清華與國運(yùn)的密切關(guān)系����,故而從浩如煙海的校史資料中擷取體現(xiàn)清華精神的珍貴部分����,以流暢的文字加以呈現(xiàn)。書中對(duì)清華的航空風(fēng)洞���、滑翔機(jī)���、防毒面具等研究項(xiàng)目以及邊疆研究會(huì)�、航空研究所等學(xué)術(shù)組織作了專門介紹�����,其立意非僅挖掘一人一事�,而在闡明清華人以國是為念,學(xué)術(shù)科研服務(wù)國家民眾的辦學(xué)宗旨��。
撥開“傳說”的迷霧
清華往事在國人口中有時(shí)像個(gè)“傳奇”�。尤其在近年來“民國熱”“名人熱”的影響下,校史上的人物�、故事真真假假,在坊間輾轉(zhuǎn)流傳����。《老照片》一書以扎實(shí)的史料和細(xì)密的考辨澄清了不少誤傳��。比如����,清華100多年發(fā)展史上��,1911-1928年為“清華學(xué)堂���、清華學(xué)校時(shí)期”,這個(gè)階段有時(shí)被誤認(rèn)為是“中學(xué)”�����,實(shí)際上并非如此����。清華開辦初衷為“留美預(yù)備”,進(jìn)行的是完整的中學(xué)教育加大學(xué)一二年級(jí)�����,正如吳景超指出的�,當(dāng)時(shí)從清華畢業(yè)赴美的學(xué)生,文科可插班大三或大四�,實(shí)科則插大二或大一。
書中《關(guān)于“破格”》一篇尤值得稱道�����。作者先舉出徐士瑚�����、張民覺�����、錢鍾書��、吳晗被“破格”錄取的例子�,這些“美談佳話”有的源自個(gè)人回憶,有的來自新聞報(bào)道����,繼而以1925-1933年清華錄取標(biāo)準(zhǔn)為依據(jù),指出這幾個(gè)人進(jìn)入清華其實(shí)都符合當(dāng)年招生要求��,均為正常錄取�����,談不上“破格”��。比如����,1925年清華學(xué)校大學(xué)部錄取分?jǐn)?shù)線是各科總平均47分���,且不考慮單科成績,而徐士瑚平均成績68分�,符合標(biāo)準(zhǔn)。錢鍾書考入清華的1929年�,錄取要求是國文英文數(shù)學(xué)三門平均不低于40分,且國文和英文不低于45分��、數(shù)學(xué)不低于5分�����,按照坊間流傳的說法��,錢鍾書數(shù)學(xué)是15分�,自然也已達(dá)線。至于吳晗���,是以插班生身份入學(xué)的�,而插班考試不考數(shù)學(xué)�����,因此也屬于正常錄取����。作者由此發(fā)出感慨“清華歷史上人才輩出,主要不是‘破格’����,而正是堅(jiān)持‘守格’的結(jié)果”。誠哉斯言����。
打撈飄散的記憶
歷史與記憶糾纏不清,而史學(xué)的根本任務(wù)是求真��,這意味著寫史者必須對(duì)記憶進(jìn)行確認(rèn)或修訂�����?!独险掌分袑?duì)清華校史上不為人熟悉的內(nèi)容的展現(xiàn),構(gòu)成了一大看點(diǎn)�����。比如���,作者以《歷史上的農(nóng)業(yè)學(xué)系》《農(nóng)事講習(xí)所》和《1934-1937年的清華大學(xué)農(nóng)業(yè)研究所》三篇文章�,對(duì)清華大學(xué)的農(nóng)學(xué)研究作了比較詳細(xì)的考證。1926年4月下旬�,清華決議成立農(nóng)業(yè)學(xué)系,“專門造就開墾人才”���,主持者為畢業(yè)于美國康奈爾大學(xué)的畜牧獸醫(yī)學(xué)家虞振鏞��。清華的農(nóng)學(xué)研究注重理論與實(shí)踐相結(jié)合�����,創(chuàng)辦了北京模范奶牛場(chǎng)����、試驗(yàn)農(nóng)場(chǎng)等�����。1928年���,農(nóng)業(yè)學(xué)系還和燕京大學(xué)���、香山慈幼院、華洋義賑會(huì)合作,組建了北京農(nóng)事講習(xí)所�����。講習(xí)所設(shè)在北京西郊�����,接近燕京大學(xué)東側(cè)�����,直接吸收農(nóng)村子弟入學(xué)����,幫助他們用較短時(shí)間學(xué)會(huì)農(nóng)業(yè)實(shí)用知識(shí)�,再回農(nóng)村推動(dòng)振興農(nóng)業(yè)。在開學(xué)典禮上�����,馮友蘭代表清華大學(xué)講話����,勉勵(lì)同學(xué)們打破舊的觀念,將來回到鄉(xiāng)間去,做一個(gè)有知識(shí)的農(nóng)民���。1930年3月12日����,講習(xí)所改名為新農(nóng)農(nóng)業(yè)學(xué)校���,取義革新農(nóng)業(yè)��、造就新農(nóng)民��。后來���,農(nóng)業(yè)學(xué)系和農(nóng)事講習(xí)所雖然結(jié)束了,但清華的農(nóng)業(yè)研究和教育仍在繼續(xù)���,1934年8月���,成立了農(nóng)業(yè)研究所,下設(shè)蟲害��、病害兩個(gè)組�����。抗戰(zhàn)期間����,清華與北大、南開組建西南聯(lián)大���,農(nóng)業(yè)研究所也隨之南遷���??箲?zhàn)勝利后,又發(fā)展為清華大學(xué)農(nóng)學(xué)院�����,為我國農(nóng)業(yè)研究與人才培養(yǎng)作出了巨大貢獻(xiàn)�����。
清華師生的事跡考證�����,是本書的又一看點(diǎn)。作者爬梳校史資料�����,打撈出不少鮮為人知的往事�����,專門挖掘了李大釗���、陳毅����、聶耳等人與清華的關(guān)系��,還以專文介紹了多名為國捐軀的清華人���。比如��,1920級(jí)校友楊光泩�����,曾任中國駐菲律賓馬尼拉總領(lǐng)事���,在菲律賓廣為宣傳中國抗日事跡���,積極為廣大華僑爭取利益。日本發(fā)動(dòng)太平洋戰(zhàn)爭后��,駐菲美軍遠(yuǎn)東軍司令麥克阿瑟撤退時(shí)����,在自己專機(jī)上給楊光泩預(yù)留了座位,但他表示:身為外交官�,未奉命令,絕不擅離職守�。1942年4月17日下午1時(shí)30分左右,不幸被日寇殺害���。1923級(jí)校友齊學(xué)啟,抗戰(zhàn)期間隨緬甸遠(yuǎn)征軍作戰(zhàn)����,中彈被俘后,堅(jiān)貞不屈����,痛斥漢奸�,彌留之際���,300多名盟軍戰(zhàn)俘為他祈禱�����,被譽(yù)為“現(xiàn)代文天祥”�。
再如��,曾任桂林�����、上?��!洞蠊珗?bào)》總編輯的著名新聞人徐鑄成�����,一般都知道他曾求學(xué)于北京師范大學(xué)�。其實(shí)���,他和清華也有一段學(xué)緣����。1926年,他以徐錫華之名考入清華大學(xué)大學(xué)部政治學(xué)系����,頓時(shí)被清華的環(huán)境所吸引,“仿佛劉阮上天臺(tái)”���。他抓緊這一學(xué)習(xí)機(jī)會(huì)���,對(duì)楊樹達(dá)、溫德�、馬約翰等清華名師留下深刻印象,而且“每晚常喜鉆入書庫��,翻閱大英百科全書及自創(chuàng)刊號(hào)起之《東方雜志》等�����,必至閉館鈴響���,始猛然驚覺,匆匆離館”����。雖然徐鑄成在清華讀書不到一年就離開了����,但“以后對(duì)她還很眷戀���,關(guān)心她的一動(dòng)一靜”����。我想�,徐鑄成的話代表了廣大清華人的心聲,而他們對(duì)母校的關(guān)注��,又寄托著深沉的民族和文化感情����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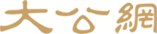


 京公網(wǎng)安備11010502037337號(hào)
京公網(wǎng)安備11010502037337號(hào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