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轉(zhuǎn)眼之間,第一次讀《追風(fēng)箏的人》(又譯作《追風(fēng)箏的孩子》)已經(jīng)是十五年前�,二○○六年的事了。
二○○八年北京奧運(yùn)����,二○一○年上海世博,二○一一年福島核洩漏……二○一九年新冠肺炎疫情��。
十五年來(lái)�����,我們所居住的這顆藍(lán)色星球�����,滾滾向前片刻不曾停歇��。
直到今年八月�,美軍撤出阿富汗,阿富汗政府在塔利班的攻擊下幾乎一夜倒臺(tái),我才再次想起這個(gè)命運(yùn)多舛的國(guó)家�����,才想起阿米爾和哈桑����,想起拉辛汗和索拉博,想起這些《追風(fēng)箏的人》中曾令我印象深刻的人物���。
“戰(zhàn)爭(zhēng)不會(huì)使高尚的情操消失����,人們甚至比和平時(shí)期更需要它����。”
“時(shí)間很貪婪──有時(shí)候����,它會(huì)獨(dú)自吞噬所有的細(xì)節(jié)?���!?/p>
“被真相傷害總比被謊言欺騙好�?����!?/p>
“安靜是祥和���,是平靜��,是降下生命音量的旋鈕。沉默是把那個(gè)按鈕關(guān)掉�,把它旋下,全部旋掉���?����!?/p>
這些是我在十五年前讀《追風(fēng)箏的人》時(shí)留下眾多摘抄中的一小部分�,初讀《追風(fēng)箏的人》�����,首先被作者卡勒德.胡賽尼(Khaled Hosseini)的語(yǔ)言所吸引���。在情節(jié)的鋪陳之中�����,他不時(shí)會(huì)寫下一些充滿哲思的文字�����,有點(diǎn)睛之效����。這些文字,如今看起來(lái)���,依然擲地有聲��。
人的一生能有幾個(gè)十五年�?一生之中又有多少書能讓你多年之后重新翻開�?十五年后,書還是那書�����,但讀書之人早已不是十五年前的自己����。十五年后�,重讀《追風(fēng)箏的人》��,少了初遇的驚艷�����,多了冷靜的思考──《追風(fēng)箏的人》��,是一個(gè)精巧的故事�����,但遠(yuǎn)稱不上一部偉大的作品�����。
書里.真實(shí)與虛構(gòu)
即使是第一次看《追風(fēng)箏的人》激賞不已的時(shí)候�,閱讀依然有一種隱隱的割裂感�。當(dāng)時(shí),這種割裂感被扣人心弦的情節(jié)所淡化��,但如今再讀����,割裂感就愈發(fā)明顯——《追風(fēng)箏的人》分為三部分�����,第一部分是一九七○年代主角在喀布爾的童年生活�����;第二部分發(fā)生在一九八○年代的美國(guó)�����,主角隨父親離開阿富汗輾轉(zhuǎn)到美國(guó)生活����;第三部分主角回到塔利班統(tǒng)治下的阿富汗�,去救贖他人和自我的救贖。割裂發(fā)生在第二和第三部分之間:前兩個(gè)部分細(xì)節(jié)豐富�、情緒飽滿,但第三部分情節(jié)太過傳奇����,巧合和偶然堆砌出來(lái)的杜撰感,讓人難以融入其中��。
其實(shí),對(duì)比一下作者本人�、書中“我”的經(jīng)歷以及阿富汗真實(shí)的歷史(見附表),似乎可以找到割裂感的源頭:
作者本人和書中“我”的年齡相仿(作者生于一九六五年����,而“我”生于一九六三年);“我”直到十八歲被迫離開阿富汗之前��,都生活在喀布爾���;作者十一歲隨父親離開喀布爾�����,除了五到八歲的三年隨父親生活在伊朗首都德黑蘭之外���,他童年的大部分時(shí)間都是在喀布爾度過的�����。正是因?yàn)橛H身經(jīng)歷留下的深刻記憶���,所以書中的細(xì)節(jié)也豐富而動(dòng)人����。
再看書中,“我”和父親由于一九七九年蘇聯(lián)出兵阿富汗�����,于是在兩年之后的一九八一年逃往巴基斯坦���,再輾轉(zhuǎn)前往美國(guó)��;現(xiàn)實(shí)中作者一九七六年����,也就是在蘇聯(lián)出兵前就隨父親前往法國(guó)巴黎�����,一九八○年全家搬到美國(guó)��。書中倉(cāng)皇赴美的不適應(yīng)�����、在美阿富汗人的生活面貌同樣是作者的親身經(jīng)歷,寫出來(lái)自然也就得心應(yīng)手���。
由于作者一九七六年之后就再也沒有回到喀布爾����,沒有經(jīng)歷過蘇聯(lián)占領(lǐng)的阿富汗����,更沒有經(jīng)歷過塔利班的統(tǒng)治,所以整個(gè)第三部分都是虛構(gòu)出來(lái)的����。作者說(shuō),這本書的起源來(lái)自他一九九九年在美國(guó)看到一則新聞�����,內(nèi)容是塔利班禁止阿富汗人放風(fēng)箏��?��?赐晷侣劊妥聛?lái)����,原本只是想寫一則關(guān)于放風(fēng)箏的短篇����,沒想到越寫越長(zhǎng)��,最終變成了現(xiàn)在的《追風(fēng)箏的人》���。
對(duì)于一部小說(shuō)而言�,虛構(gòu)絕不是問題�����,問題在于作為一部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作品���,《追風(fēng)箏的人》虛構(gòu)得并不成功�。為了讓書中的“我”完成精神上的救贖�����,作者特地或者說(shuō)強(qiáng)行讓成年之后的“我”再次面對(duì)自己童年噩夢(mèng)的根源──對(duì)“我”造成巨大童年創(chuàng)傷的人���,如今就是阻止“我”救走童年好友之子的人����,而且作者為這一“最終boss”賦予了純粹的“惡”:他已經(jīng)從當(dāng)年的惡童,變成集暴力����、變態(tài)、兇狠�、殘忍于一身的塔利班頭目。而“我”則如同眾多荷里活電影中的英雄人物一樣����,在強(qiáng)大精神力的支撐之下,由原本的柔弱變得堅(jiān)不可摧��,不但孤身一人深入敵人重兵防守的老巢��,而且干掉了罪魁禍?zhǔn)?�,最終帶著象征著希望的孩子逃出生天��。第三部分人物的臉譜化���、情節(jié)的英雄化����,與前兩部分建立在真實(shí)基礎(chǔ)上的還原格格不入��,造成了前文所提到的“割裂感”����。
書外.喀布爾與喀什
再看小說(shuō)出版的時(shí)間,是在美軍占領(lǐng)阿富汗之后的二○○三年��,“剛好”書中虛構(gòu)出來(lái)的��、集合人性之惡于一身的罪魁禍?zhǔn)?�,其身份又是塔利班的頭目�����。無(wú)形之中���,讓整個(gè)塔利班被妖魔化�����、面具化���、扁平化了���。這符合當(dāng)時(shí)整個(gè)西方社會(huì)對(duì)于塔利班的想像,也無(wú)疑正義化了美軍的入侵行為�。
諷刺的是,美國(guó)電影公司派拉蒙在二○○七年拍攝電影《追風(fēng)箏的人》時(shí)�����,由于美軍占領(lǐng)之下的阿富汗危機(jī)四伏�����,攝制組沒能前往阿富汗實(shí)地拍攝�,而是最終選擇了與喀布爾地貌、環(huán)境都極為相似�����,但安定繁榮的新疆喀什來(lái)拍攝外景��。
一個(gè)是美國(guó)以重建民主���、自由為名悍然入侵����,駐軍之后卻依然支離破碎的阿富汗,一個(gè)是美國(guó)以“人權(quán)”為名肆意詆毀的新疆�����,他們卻選擇了后者�。在生命安全面前���,他們“嘴里說(shuō)不����,身體很誠(chéng)實(shí)”�����。
尾聲
電影版《追風(fēng)箏的人》基本上忠實(shí)于原著小說(shuō)���,但書中有一個(gè)重要情節(jié)沒有重現(xiàn)���。電影中,主角阿米爾將童年伙伴哈桑的遺孤索拉博從喀布爾救出來(lái)之后�����,沒有經(jīng)過什么波折就順利地到達(dá)了美國(guó),而小說(shuō)中�,他們?cè)诎突固苟虝和A簦溟g由于無(wú)法證明索拉博是孤兒�,所以無(wú)法取得美國(guó)簽證,索拉博甚至因此而割腕自殺����。
盡管在生死關(guān)頭被救回來(lái),但索拉博還是情緒低落����,主角問他:“我能做什么,索拉博��?請(qǐng)告訴我��?���!彼骼┱f(shuō):“我想要爸爸和親愛的媽媽,我想要莎莎�����,我想要跟拉辛汗老爺在花園玩�����,我想要回到我們的房子生活?���!彼们氨凵w住雙眼,“我想要回到原來(lái)的生活�。”
合上《追風(fēng)箏的人》���,看著新聞報(bào)道中匆忙撤退的美軍,以及他們背后斷壁殘?jiān)目Σ紶?,我想這大概是每一個(gè)阿富汗人的心聲吧──“我想要回到原來(lái)的生活?����!?/p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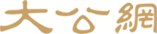


 京公網(wǎng)安備11010502037337號(hào)
京公網(wǎng)安備11010502037337號(hào)